 “人没法给出自己没有的东西。”
刚结束一场两小时的谈话,对方走后,我盯着窗外的梧桐叶发了很久的呆。他说自己总在关系里感到窒息,付出全部却换不来理解,可我分明在他的讲述里,看到了曾经的自己——那个习惯把“我没事”挂在嘴边,却在深夜翻来覆去的人。
很多时候,我们以为“关注别人”是一种能力,却忘了这份能力的起点,是先站稳在自己的土地上。就像园丁照料花木前,要先知道自己的水壶里有没有水,若是提着空壶忙碌,最终只能看着枝叶在烈日下枯蔫。
看见自己的褶皱
初入行时,我总想着“要帮对方解决问题”。有位来访者说起职场中的委屈,领导的否定让她整夜失眠,我立刻列出三条应对建议,语气笃定得像在宣读标准答案。可她只是低着头,手指反复摩挲着咖啡杯沿,轻声说:“其实我只是想有人知道,我已经很努力了。”
那瞬间我突然意识到,我递出的“解决方案”,不过是在掩盖自己的慌张——我害怕面对她的脆弱,就像害怕承认自己也曾在被否定时,偷偷躲在楼梯间掉过眼泪。后来我学着放慢节奏,在开口前先问自己:“此刻我心里涌起的,是她的情绪,还是我的?”
看见自己,从来不是挑出优点或缺点,而是允许自己有褶皱。就像刚拆封的书页难免卷边,我们不必急着把它压平,只需承认“它现在就是这个样子”。有位母亲说孩子总不听话,讲到激动处声音发颤,我感到胸口一阵发紧——那是我想起了小时候,母亲也总说“我都是为你好”,而我攥着拳头躲在门后。等我轻轻吐出一口气,对她说“被孩子顶撞时,心里一定又急又疼吧”,她突然红了眼眶,说这是第一次有人懂她的感受。
原来当我们坦诚面对自己的褶皱,那些藏在褶皱里的情绪,会变成理解别人的钥匙。
“人没法给出自己没有的东西。”
刚结束一场两小时的谈话,对方走后,我盯着窗外的梧桐叶发了很久的呆。他说自己总在关系里感到窒息,付出全部却换不来理解,可我分明在他的讲述里,看到了曾经的自己——那个习惯把“我没事”挂在嘴边,却在深夜翻来覆去的人。
很多时候,我们以为“关注别人”是一种能力,却忘了这份能力的起点,是先站稳在自己的土地上。就像园丁照料花木前,要先知道自己的水壶里有没有水,若是提着空壶忙碌,最终只能看着枝叶在烈日下枯蔫。
看见自己的褶皱
初入行时,我总想着“要帮对方解决问题”。有位来访者说起职场中的委屈,领导的否定让她整夜失眠,我立刻列出三条应对建议,语气笃定得像在宣读标准答案。可她只是低着头,手指反复摩挲着咖啡杯沿,轻声说:“其实我只是想有人知道,我已经很努力了。”
那瞬间我突然意识到,我递出的“解决方案”,不过是在掩盖自己的慌张——我害怕面对她的脆弱,就像害怕承认自己也曾在被否定时,偷偷躲在楼梯间掉过眼泪。后来我学着放慢节奏,在开口前先问自己:“此刻我心里涌起的,是她的情绪,还是我的?”
看见自己,从来不是挑出优点或缺点,而是允许自己有褶皱。就像刚拆封的书页难免卷边,我们不必急着把它压平,只需承认“它现在就是这个样子”。有位母亲说孩子总不听话,讲到激动处声音发颤,我感到胸口一阵发紧——那是我想起了小时候,母亲也总说“我都是为你好”,而我攥着拳头躲在门后。等我轻轻吐出一口气,对她说“被孩子顶撞时,心里一定又急又疼吧”,她突然红了眼眶,说这是第一次有人懂她的感受。
原来当我们坦诚面对自己的褶皱,那些藏在褶皱里的情绪,会变成理解别人的钥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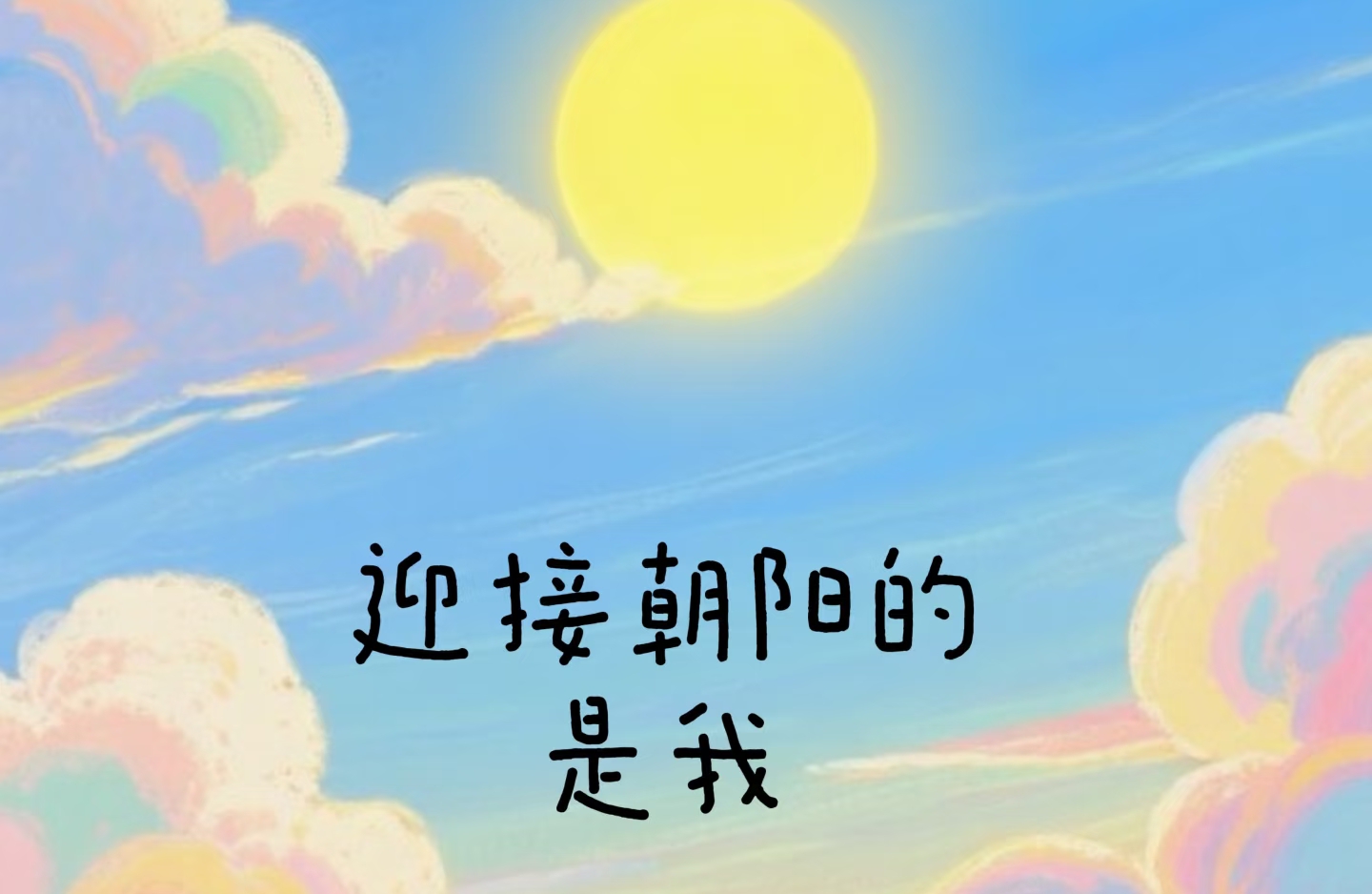 空杯子才能盛水
朋友曾问我:“每天听那么多烦心事,会不会觉得累?”我想起工作室的玻璃杯,每天结束后都会认真清洗,倒过来沥干水分。若是前一天的茶渍没擦干净,第二天泡的茶总会带着杂味。人的心也是这样,若装满了自己的执念、焦虑、未完成的期待,就腾不出地方承接别人的故事。
有位来访者每周三下午来,总说丈夫不够体贴。起初我总忍不住想“她应该更独立些”,直到某天发现,这个念头其实来自我对父亲的抱怨——小时候他总忙于工作,很少陪我去公园。当我在心里对自己说“原来我还在期待被更多关注啊”,再听她说话时,耳朵里就少了评判的杂音,能听见她语气里的失落:“其实我只是想他回家时,能问一句我今天过得好不好。”
清空自己,不是变成没有情绪的石头,而是像海绵吸水后轻轻挤干,保持柔软却不沉重。有次来访者迟到了四十分钟,进门时反复道歉,我笑着说“路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”,而不是在心里盘算“这会影响接下来的安排”。她愣了愣,说女儿突然发烧,送完医院一路跑过来,“您没生气,我反而更过意不去了”。那天她讲了很多作为母亲的挣扎,而我只是坐在那里,像捧着一碗温热的粥,不急不躁地等她慢慢说。
空杯子才能盛水
朋友曾问我:“每天听那么多烦心事,会不会觉得累?”我想起工作室的玻璃杯,每天结束后都会认真清洗,倒过来沥干水分。若是前一天的茶渍没擦干净,第二天泡的茶总会带着杂味。人的心也是这样,若装满了自己的执念、焦虑、未完成的期待,就腾不出地方承接别人的故事。
有位来访者每周三下午来,总说丈夫不够体贴。起初我总忍不住想“她应该更独立些”,直到某天发现,这个念头其实来自我对父亲的抱怨——小时候他总忙于工作,很少陪我去公园。当我在心里对自己说“原来我还在期待被更多关注啊”,再听她说话时,耳朵里就少了评判的杂音,能听见她语气里的失落:“其实我只是想他回家时,能问一句我今天过得好不好。”
清空自己,不是变成没有情绪的石头,而是像海绵吸水后轻轻挤干,保持柔软却不沉重。有次来访者迟到了四十分钟,进门时反复道歉,我笑着说“路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”,而不是在心里盘算“这会影响接下来的安排”。她愣了愣,说女儿突然发烧,送完医院一路跑过来,“您没生气,我反而更过意不去了”。那天她讲了很多作为母亲的挣扎,而我只是坐在那里,像捧着一碗温热的粥,不急不躁地等她慢慢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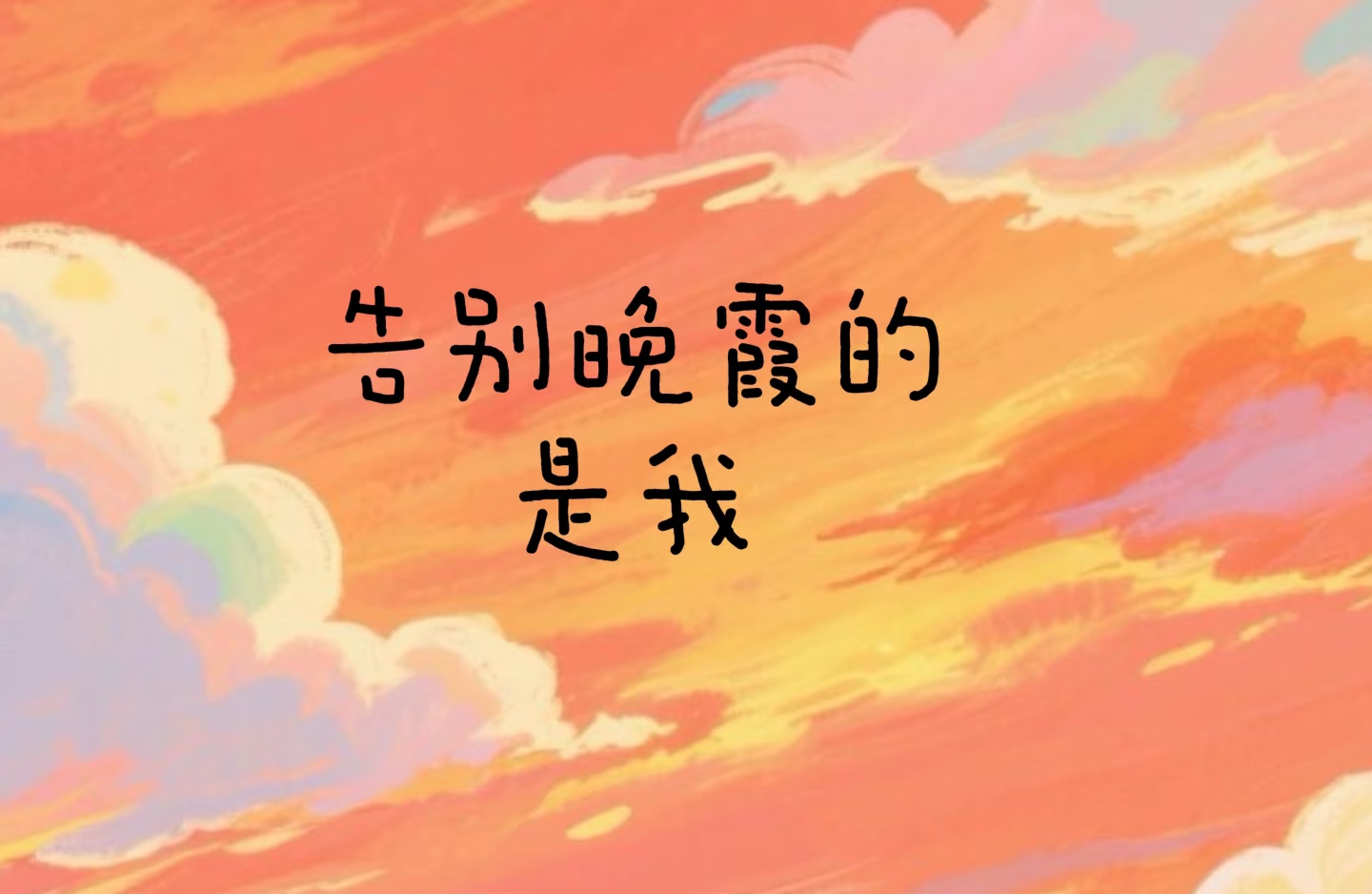 光会照亮彼此
有位老人每周来读自己写的诗,他的手抖得厉害,字总歪歪扭扭落在稿纸上。起初我觉得他的诗“没什么章法”,直到某天读到一句“月亮把影子拉得很长,像我没说出口的牵挂”,突然想起爷爷临终前,攥着我的手想说什么,最终只化作一声叹息。我抬头对老人说:“这句诗里,藏着好多舍不得啊。”他浑浊的眼睛里,突然泛起了光。
后来我渐渐明白,先看见自己,不是为了沉溺于自我,而是为了拥有一份清醒的温柔。就像先摸清自己的体温,才能准确感知别人的冷暖;先接纳自己的不完美,才不会在看见别人的裂痕时,下意识地躲闪或指责。
工作室的窗台上,常年放着一盆绿萝。有时阳光太烈,叶子会蔫下去,我从不急着浇水,而是先摸摸土壤的干湿。就像面对那些坐在对面的人,我不再想着“要做些什么”,而是先稳住自己的呼吸,知道此刻的沉默里,藏着比语言更珍贵的东西——那是两个灵魂在彼此看见时,悄悄生长出的,温柔的力量。
光会照亮彼此
有位老人每周来读自己写的诗,他的手抖得厉害,字总歪歪扭扭落在稿纸上。起初我觉得他的诗“没什么章法”,直到某天读到一句“月亮把影子拉得很长,像我没说出口的牵挂”,突然想起爷爷临终前,攥着我的手想说什么,最终只化作一声叹息。我抬头对老人说:“这句诗里,藏着好多舍不得啊。”他浑浊的眼睛里,突然泛起了光。
后来我渐渐明白,先看见自己,不是为了沉溺于自我,而是为了拥有一份清醒的温柔。就像先摸清自己的体温,才能准确感知别人的冷暖;先接纳自己的不完美,才不会在看见别人的裂痕时,下意识地躲闪或指责。
工作室的窗台上,常年放着一盆绿萝。有时阳光太烈,叶子会蔫下去,我从不急着浇水,而是先摸摸土壤的干湿。就像面对那些坐在对面的人,我不再想着“要做些什么”,而是先稳住自己的呼吸,知道此刻的沉默里,藏着比语言更珍贵的东西——那是两个灵魂在彼此看见时,悄悄生长出的,温柔的力量。




